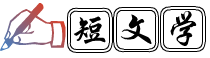北京某特殊病房,要不是一些医疗装置和穿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进出,你会认为那是一个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。
冷心蝉,一个八十岁以上的男子,躺在病床上,鼻孔插着氧气导管,床边有输送点滴的支架。说话总是一顿一顿的。
侯伯归,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子,坐在床边的一个凳子上。
王斧,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子,医生,身着白大褂。
护士,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女子。
冷心蝉:听说,病房很紧张……
侯伯归:老同志总是喜欢冬天生病。但为像您这样的老人,病房总是有的。
冷心蝉:又把谁挤出去了?
侯伯归:没把谁挤出去,都是病人,挤不走的,外面还排着队往这儿送。医院会留出一些空置病房的,时刻准备着。
冷心蝉:我这次恐怕躲不过了。
侯伯归:您放心,您过得去。我们都相信您能过得去,就像过去每回那样过得去。
冷心蝉:你说的“我们”是指谁?
侯伯归:“我们”就是他们。
冷心蝉:噢……他们。
静场
——重庆那边怎么回事?
侯伯归:(惊讶而疑惑地)小季出了点事情。
冷心蝉:恐怕那事情不能称为“一点”吧。
侯伯归:这事遮得住就小,遮不住就大。
冷心蝉:到底是“遮住”,还是“遮不住”啊?
侯伯归:现在还在遮,到底“住”还是“不住”,要走着瞧。
冷心蝉:遮,未必就是好办法。
侯伯归:但“不遮”也不是办法。
冷心蝉:恐怕事情坏就坏在——遮而没遮住。
侯伯归:都是自己人出卖了秘密。
冷心蝉:自己人?!唉……这帮自己人!怎么会连自己的保镖都管不住。
侯伯归:他当众煽了保镖一记耳光。保镖觉得伤了自尊,怀恨在心,所以出卖了秘密。
冷心蝉:一记耳光就能让保镖变心?!看来他并不是个善于用人的人。
侯伯归:现在跟过去不同了,年轻人不好带。
冷心蝉:今年,重庆不会有大的业绩了。南京怎么样?
侯伯归:小罗做得还可以,这是保住公司业绩的一块。幸亏有了南京……
冷心蝉:南京不能再丢了。
侯伯归:南京不会丢。国外的同行会幸灾乐祸的。他们就在等这样的机会。
停顿
冷心蝉:重庆方面就那么爱唱歌?!
侯伯归:小季深受西方文艺的影响,总想把重庆那块搞得文艺一些。
冷心蝉:他们都唱什么歌?民歌吗?
侯伯归:大合唱,一些老歌。
冷心蝉:老歌?!老歌还有谁爱听?
侯伯归:本来是一些老员工自娱自乐,可非逼着年轻人跟着掺合。
冷心蝉:年轻人应该有他们自己的歌,连这个道理小季也不懂?!
侯伯归:他也许觉得老歌才是经典。
冷心蝉:经典中也要有时代精神……他知道时代精神吗?
侯伯归:他恐怕没弄懂时代精神。
冷心蝉:一个五十来岁的人怎么连时代精神都弄不懂?
冷心蝉一阵咳嗽,整张脸憋涨着。侯伯归起身为冷心蝉轻轻捶背,使之平复下来
……时代精神,这体现在方方面面。我们现在不只限于国内业务,也有国外业务,我们是一个国际化的大公司了。公司文化应该体现国际性。他们为什么没有用意大利的咏叹调唱唱我们的越剧《梁祝》?
侯伯归:他们可能没那嗓门。
冷心蝉:说到嗓门,对了,你夫人是个歌唱家。她现在怎么样?
侯伯归:她现在不唱了。唱歌,还是年轻时候的事情。
冷心蝉:她为啥不唱呢?
侯伯归:在家当全职太太。我整天这么忙。
冷心蝉:你看这叫什么事?会唱却不唱,不会唱的到整天唱,各种大奖赛得唱。
停顿
女人也应该有自己的事业追求。如果为了当全职太太,你干嘛当初娶个有歌唱才华的人?有机会还是让她放歌吧!
停顿
……你们家的西瓜怎么样?
侯伯归:西瓜?!你说的是我们家的冬瓜吧?
冷心蝉:对,冬瓜。
侯伯归:冬瓜去美国留学了。
冷心蝉:留学好,国内连个像样的大学也没有。孩子们都应该出去学学。
侯伯归:其实,跟美国也学不了什么东西。尽带回来一些坏习惯。
冷心蝉:他学什么了?
侯伯归:法律。
冷心蝉:这个可以回国使吗?你们可要看好你们的孩子,别让美国给偷了。
侯伯归:时代确实在变。孩子已经不是我们的孩子了。
冷心蝉:在我和你父亲向你们交班的时候,我们总是喜欢让老大从政,老二从商。这样才使家族事业横跨政商两界。可如今,你们都仅有一个孩子。所以,我们倡导你们联姻。你们如果不团结,就无法联姻;你们不联姻,这公司最终会旁落于人。这公司的血脉要怎么传下去?
在我担任公司法人代表期间,我就曾要求你和季家联姻,让冬瓜娶他们家的梅花。可你们都由着孩子……如今,闹出这“小季要进董事会”的丑剧……
侯伯归:进董事会可不是靠发动员工去唱歌!公司经营不是看谁嗓门嘹亮,得看经营业绩。要比唱歌,我夫人韦莉可是歌唱家出身……
冷心蝉:这也不能怪他,性格使然。业绩搞不上去,就想在文艺方面做出点样子。他显然想跟你比拼,你很年轻时就搞了艺术家,他只有通过搞艺术才能当家。
停顿
事情闹到北京来,其它的董事们都怎么看待这件事情?
侯伯归:董事们都觉得小季这事做得不妥。
冷心蝉:何止是不妥?简直逆天了?进董事会得看全体股东的意见。
停顿
事实上,我们也没有让全体股东进行投票。
停顿
我们是受过苦的一代人,知道猫是怎么一回事。鼠疫,是猫的一个阴谋,用来吓唬人的。猫有爬树的本领,天上地下的,上串下跳。那时候老鼠多,我们都依赖猫。但最终猫被惯坏了。它抓了我们,在我们身上留下了伤痕。如今这时代老鼠越来越少,老鼠已经不再是时代的隐患了。猫已经失去其重要性了,它沦为宠物。给它狗粮吃,还是不给它狗粮吃,得看我们这些主人的脸色。
猫,曾经是我们的祸患。那时,我们以为鼠疫才是我们的祸患。猫是老鼠时代的骄子,它控制过世界。
停顿
——你们的父辈和我一样都打过硬仗,这个你们不会忘记。但是,你们不能永远躺在父辈的战绩上。再说了,你们的父辈都打的什么人?打的是自己的兄弟啊。他们把祖传家业抢到了手,这个很好。可是,你们如今不能再兄弟相残了。兄弟相残,这不能成为家族的传统。
侯伯归:是的,冷伯。
冷心蝉:我不冷。这氧气输进肺里,像喝了蜂蜜。
停顿
——毕竟,时代不同了。你们知道什么是股份制吗?股份制,就意味着这公司不再仅仅属于你们家族的了。我们的分公司都覆盖了全国,我们是全国性的公司。我们不是要求每个员工都树立主人公精神吗?
公司虽然发源于上海,可如今总部毕竟已经迁到北京了。所以,我希望你们以后在董事会上不要再讲上海话,什么“阿拉侬的”?北京话既然作为普通话的基准,自然有它的道理,所以,你们倒可以多吊吊北京腔,跟地道的北京人混个熟。我们毕竟是一个全国性的公司,各个分区经理来的时候,你们更不要突出上海的某种传统。聚餐的时候,一定非要吃甜食吗?为啥就不能吃吃北方的拍黄瓜?
上海话,对外地人就像泥泞小道,没多少人能在上面行云流水。我知道,上海话不难听,我自己在家也讲上海话。但是,我从来不会在会议上讲上海话,在北京我们不能让上海话走出自己的家门。这如今是我提出的一个要求。
我们不是也离开上海很多年了吗?这是一个造词的时代。每个地方都开始有自己的语言了。上海流行的许多新词,这不是在北京的上海家庭都能懂的,上海话还是走不出上海。
停顿
如今,你们还想再闹什么呢?小季的事情,我们一定会认真严肃地处理。竟然,闹出这种事?
侯伯归:这事弄不好,没准阴沟里会翻了大船。
冷心蝉:这可不是阴沟,估计是片深海。他也许早就想葬身深海了。这种事一出,我真替他的家属难过。
侯伯归:这事您放心,他夫人就是个律师,他们应该懂得如何摆平这个事情。
冷心蝉:这已经超越了法律的范围了,律师能顶个屁用?如果,他那律师的老婆能给他指出法律可行的路径,他就不至于走到这一步。
停顿
我主要考虑到他老爸。这么多年的交情,叫我如何处置是好?
侯伯归:是的,冷伯。
冷心蝉:我不冷。
传来几声轻微的敲门声,随后,王斧身着白大褂走了进来。他盯着那悬挂的药水瓶看了一眼。
王斧:您怎么样?
冷心蝉:我很好。
(用手轻轻指了下侯伯归)这是我们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侯伯归先生。
王斧:我认识侯先生。他大名鼎鼎。
侯伯归:哪里,哪里!冷伯的健康全靠您了。
王斧:这是腔隙性脑梗塞。上了岁数的老人,如今得心脑血管方面疾病的甚多,这个需要随时防范。
冷心蝉:给医院添麻烦了。
王斧:谢谢您老选择我们医院。
王斧按了一下床边的呼叫器,一名护士走了进来。
护士:主任,你叫我?
王斧:把给冷老配好的进口药拿过来。
(护士转身出去取药)
这人的脑子好不了!这脑子里有云团了!(王斧举着一张CT透视胶片,胶片上一个头骨图案。)这脑子跟动物的脑子有什么区别?就因为被围困在人的颅腔以内?那沟回还很深吗?在沟回中游荡的阴茎一样的小颗粒是什么?
停顿。
幸亏时代变了。
幸亏这个世界还有死亡这件事。否则,这帮权贵会有求助于我们的时候?幸亏有癌症,有脑梗塞,有心肌萎缩,有游走性神经疼,有各种病毒,有痔疮,有溃疡,有交通事故,有火灾烧伤,有捅刀子的打架斗殴……这世界需要伤痛,需要死亡。没有伤痛和死亡,人们又怎么会珍惜生命。否则,我们医生就失去意义,世界上也就不存在医生这个行当了。
如果时代没变,我就治不了别人的脑子了。相反,我的脑子一定会被一种红色的粘稠状的血浆堵塞了。在我青少年时,他们就整天给我们的大脑输送意识形态的血红蛋白。
如果,没有医生这个行当,我会做什么?我会从政,还是经商?作为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,没有任何背景,无论是经商还是从政,我都必须寻找靠山。可那是一条表面光明的黑路。他们的发达是建立在别人的尸体上的。
停顿。
说得尸体。这是对医生职业的一种否定。我拒绝还他们一具尸体。他们躺着进来,我总需要千方百计地让他们站着出去。可如今这脑海深处的暗团,会让他成为一具真正的尸体吗?
但愿那些白色的、黄色的药丸能起作用,那些透明的跟水差不多颜色的药液能起作用。要不,可需要用上我的小斧头了。
冷心蝉:(以哀伤失望的表情)如今,拯救脑组织还得用进口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