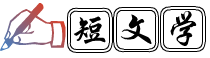我头发都白了。
曾经尝试染发,可头发生长得极快,白发根冒出来,对比着紫发黑发,更是难看,效果不理想,我就不去染发了。
我的皮肤还很年轻,也很滋润,我夸耀自己可以靠黄化妆品公司,毕竟,一个冬天敢洗完脸就出家门的没有几个。
早晨,我戴上口罩去买菜。
换身清爽的衣服,推着破车,难的的好天气。
天空很美,从地面看去,满天的白云彩,把碧空挤得歪歪斜斜,鸟儿弹丸般掠出去,引得我仰脖子去看,他们划出孤影,飞远了。
集市很热闹,人群熙熙攘攘,买的卖的,大家都高高兴兴的。
我依着破车站立,人们从我身边流过去,小狗们钻过来,在大鱼盆前探头探脑。
我来买菜,主要是买小猫鱼。家里三个毛孩子,都要吃鱼。
他们骗不得的!你也骗不了他们。
他们在院子里趴着吃食,我在屋子里坐着吃饭,他们竟然吃出高我一等的感觉。
我可以吃素,他们不能吃素,他们要吃鱼或者肉,饭盆里没有荤腥,他们连闻都不会闻,瞅一瞅,再哀怨地看看我,扭头躺在垫子下,这垫子肯定放在最暖和的阳光里,毛孩子用前爪握住脑袋瓜儿,翻翻白肚皮,扭扭腰板,连瞅我都不会。
三个毛孩子,要吃不少东西。他们甚至比我们母女吃得多,吃得精,吃得没有任何压力。
我想一切方法哄弄他们。
“看看!”我分一盆饭,“这里面好多鱼啊,妈妈最爱杜大皮,这是给杜大皮的!杜大皮刚生了小孩子,需要补一补!”
杜大皮不识数,可听的懂话,她看看饭盆,再闻闻小鱼,高高兴兴吃起饭来。
“这是给杜大黑的”我又分一盆饭,这饭里少放一条鱼,多放了鱼汤,“杜大黑会看家,妈妈多给些好吃的!”
杜大黑识数,听的懂话,但是,她懒得搭理我,因为她有饭门,她跟卖肉的张伯伯很投缘,她每天都去帮张伯伯做买卖,可以当发财狗,她为了照顾我的面子,懒洋洋地吃口食。
“这是给杜老白的”我又分一盆饭,这饭里都是馒头面条,很小一条鱼,“杜老白长身体,得多吃多喝!看看,妈妈把好料都留给我大老白了!”
杜老白又懂话又识数,可他会装傻,做为全家唯一男孩子,他不愿意跟我计较,他吃了自己盆里的饭,就去吃杜大黑的饭,大黑是他的妈妈,更不会跟他计较。
家里没有鱼了,毛孩子不肯吃食,没有鱼,他们就不愿意装装样子了,四散躺着,杜大皮的崽崽撕心裂肺的“嗷嗷叫”,我怎么能听得下去?
集市有的是卖鱼的,我得早起去买鱼。
我站在鱼盆前,许多的鱼啊!他们在鱼盆里,看着我。
我蹲下去,手伸进盆里。
从我这个位置,可以看到我的头发。
我站起来,跟摊主讲价钱。
摊主是个老大爷,口罩蒙着半截脸,他头发雪白雪白的,漏着两只眼睛。
“您……”这大爷说,“这鱼……”
我停了下来,街市突然喧闹起来,地面的蔬菜仿佛重新生了根,他们葱茏起来,我眼前金花乱坠。
我眨眨眼睛,好像出现了幻觉,摊上的猪肉都长了脚,啪啪地跑过来,我只觉得目眩。
“您……”摊主又说,他带一点乡音,“您了……”
他更客气了,晨曦里,他的发越发雪白,头皮铮亮,他的额头布满皱纹,他疑惑地看看我。
我握握车子,努力撑直身体。
“您说什么?”我问到。
“哦!”他说,“我告诉您价钱!您了可以少给这个零儿。”
他很困惑,看看我,“您还买吗?这已经很便宜,不能再划价了。”
我咽口唾沫,急忙掏钱,付了帐,捏着这鱼回家。
我觉得沮丧,这老大爷喊我“您”!他不见得是客气,他认为我跟他一样老了吧?我宁可他不跟我客气!我宁可他称呼我“你”!我忽然没有了逛菜市场的兴趣。
我找了个玻璃柜台,这玻璃毛毛的,积满灰尘,却可以当镜子照。
我把脸对着这毛镜子,我审视自己的眼睛,眨眨眼睛,我观察眼皮,光滑的眼皮有了细腻的纹路。
我将近五十岁,我想。
然后,我低下头,看着头顶的倒影。
发如雪了。
我的发如雪了。
我伸手,拨动头发,这发簌簌地颤动,白发压住手指,手指依然修长,却有了深纹,失去了柔软的触觉。
我的发真的如雪了。
我露出口鼻,看着自己的容颜,仔仔细细看着,胆怯地拂去肌肤存留的岁月,慢慢搓磨痕迹,不管怎样,我已经老了。
一晃就老了。
我呆住,又去眺望蓝天,这美丽的天空越来越清澈,而我,越来越老了。
我定定地看着柜台,柜台荒置许多年,边角缝里,长出了嫩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