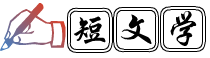总是期待有朝一日乘着极速飞船,追回所有流逝的时光。我就能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站在远去的时代里,看看自己婴儿时的模样,现场体验母亲对我抚育的场景。然而愿望毕竟与现实有很遥远的距离。与其这样幻想下去,倒不如打开记忆的扉页,重拾母爱的片段……
写字台里卧着一把木尺,长约一尺五寸。表面痕迹斑斑,残缺不全。然而听父亲说过,在我刚出生时,它却是母亲丈量尺寸的唯一工具。
煤油灯下,母亲拿出杂陈碎布的针线盒。右手中拇指戴上顶针,一针一线将布头串在一起。均匀铺平棉絮,缝成靴子的形状。母亲做好一双完整的“棉蹄蹲”,需要好几个夜晚连续奋战,有时竟然熬到一两点钟。鸡鸣报晓还是像往常一样准时,并没有推迟一丁点。毫无照顾母亲睡眠的意思。每当东方天空泛起鱼肚白的时候,母亲已经在生产队田里忙活一阵子。由于体力不支,她曾晕倒在田里好几回。不但没受到队里的同情,反而还被扣了“工分”。母亲没有怨言,更不提为自己辩护了。回到家中,看到我趴在家人的肩上,穿着她赶制的“棉蹄蹲”时,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。不知道她熬了多少个日日夜夜,为我们兄弟幼儿时做了多少双这样的“棉蹄蹲”?但我知道她是用那把木尺计量“棉蹄蹲”长度的。
三岁的时候,我也混迹过“江湖”,算是丐帮的一名弟子。原来每每忙完队里的农活,父母就会把哥哥丢在家里。背上我到外面讨饭,这在当时算是额外营生的一条路。夏日炎炎,瘦弱不堪的我,像一个细挑的小南瓜。满身火疮,总会趴在异乡的井沿边。别人家的孩子穿梭嬉戏,激不起我丝毫的参与兴致。而我只是耷拉着脑袋,用手挠着流出很多脓液的疙瘩。
母亲看在眼里,疼在心里。总会带着痛苦的语气说:“这孩子,我怕拉扯不大了。”好在天无绝人之路,母亲爱子之情打动了当地的一位妇女。借着夜色的掩护,她在晚上引领母亲步行十几里之外采摘蚕豆。凌晨时分,用陶瓷罐煮熟。盐味十足,勾起孩子的食欲。自那以后,我的身体渐渐好转起来。其他的食物在干部的眼皮底下得以逃脱,都被我独自享用。而在母亲的人生里,却写上一段不光彩的“偷窃”履历。后来邻家大娘又给我弄来药膏,抹好了毒疮。
现在我从父亲口里获知,那时逃难的地点是宿州的西子坡。安静的时候,脑海中总会浮现捏吃的一个个豆粒。那豆里究竟充斥着母亲多少个脚步?她的额头上滑落多颗汗滴?好在那把木尺已经烙印心底,宛若一个方程式,解得母爱的厚度是一个极值!
十七岁的夏天,雨季来得太猛烈。在人们祈祷声中,雨水终于止步。不可思议的事竟又发生,几个月后,秋雨才姗姗来迟。好多旱物庄稼错过时节。我家被逼无奈,种了十几亩绿豆。家里经济拮据,勉强凑足我上师范念书的学费。至于生活费,家里只能按星期提供。我知道钱凑之不易,那是母亲采摘绿豆所得。
十几亩的绿豆长势很好,母亲拽完这块地豆子,还没有来得及休息。那块地豆皮又发黑了,只得连天采摘。母亲劳累过度,眼角肿胀起来。我在双休日总会协助母亲大战“绿豆城”。累的时候,母亲总会让我到田埂上歇息。我静静地望着田地,记住母亲摘豆的每个姿势。左手挎着竹篮,低下头,弯着腰。右手拽掉豆子,快速地撂进篮里。有时遇到好豆子连在一起,她就会放下篮子。双手连连采摘,不住地弯腰点头,好像给土地神作揖似的。母亲犹似那勤劳的蚕虫伏在叶上。一棵棵,一片片,都留下她采撷过的指纹……
每次母亲为我积攒的生活费,总有满是皱纹的零碎纸币,当然也不缺乏沉甸甸的铁疙瘩。为了让我携带方便,经常会到小店兑换成整钱。每当接过她手中的钱,我的心就震颤起来。脑中的尺子顿时浮现,丈量起母爱的深度,简直深不见底。
母亲的那把木尺,现在很少使用。它的长度虽然有限,却丝毫不影响我对它的珍藏。拥有这把刻上苦涩岁月的尺子,我就可以丈量母爱的尺寸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