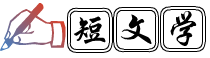毛之周,一个五十多岁男子。
邓江,一个四十岁女子。
一个拥有毛玻璃门卫生间的旅馆房间。
一张床,被褥整洁地码放,显然无人动过。
房间内有暖色光源,邓江站在窗前,望着外面。透光卫生间的毛玻璃,能见到一个模糊的身影,毛之周坐在马桶上,不时有憋气与舒气的声音和应答声,烟蒂的火焰一闪一闪的。
整体气氛安详而静谧,毫无紧张感。场景一直展现为房间,镜头一直追随邓江。邓和毛的声音一点都不激昂。
邓江:他们都是些什么人?
毛之周:他们注定不是我们。
邓江:他们真的能够宣布与我们不是同一类人?
毛之周:他们为什么要宣布?他们不需要宣布,他们本来就不是……
邓江:他们为什么要走左线?难道他们认识不到通往未来的正确方向在右边?!
毛之周:他们认为那种“正确”是你们的?虽然,全世界都在右边。
邓江: 哪种“正确”?
毛之周:“正确”难道仅有一种?
邓江:他们说那种“正确”是一种邪路。他们内心仅愿意走在老路上,可他们说不要走老路,但是他们还是走在老路上,他们也高谈创新和改革。
毛之周:唯老路是邪路。他们也在改,往更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改。
邓江:他们说那是一种正确。
毛之周:那是一种具有他们自身特色的正确。正确,需要从特定的视角来讲。正确是一种白色的光线,照在不同颜色的物体上,反射着不同的颜色,他们认为正确仅能是红。
邓江:可是,大家都知道,红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不正确的,红代表不了正确。世界人有很多人用自己的颜色也证明了红不是正确。
毛之周:可是,他们不让大家看外面,他们要大家仅看着屋子里面。屋子里布满了红,他们使用了红色的灯泡,那是一种高瓦数的意识形态的灯泡。
停顿。
大灯泡晃着,照耀着房间,他们想让外面陌生化,他们想塑造另一个仅属于他们的世界,他们还有把他们塑造的世界当成人们唯一的世界。
邓江:他们?……
毛之周:一个陌生人走过来,你不认识他,你问他们“那人是谁?”他们会怎么回答你?
邓江:(转过脸,望着卫生间的毛玻璃,看着里面的人影)他们会怎么回答?
毛之周:他们会这样向你介绍那个陌生人:“那是一个具有他自己特色和属性的人”。他们也这么回答你什么叫时下的中国。
有一种社会理论叫“狗屁不通”。
邓江:真正的“狗屁不通”。
停顿。
你通吗?关键时候就拉稀。
毛之周:我不是在拉稀,我这是便秘。
邓江:你总是从问题的一端走向另一端,你从来就不能中庸处事。
毛之周:我生来受的就是一种反中庸的教育,这决定了我不是拉稀就只能便秘。
邓江:你已经拉了多久了?少说也有一顿饭的功夫。
毛之周:我没有生在大饥荒时代,小时候,家长关于吃饭的教育就是细嚼慢咽,这使得一顿饭的时间很长。吃饭,是美好的时光。我们应该懂得享受这样的时光。拉屎,也是一种放松人生的时刻。
邓江:……我一出生,就被我爸带进部队,和一群士兵抢饭吃。我爸时常跟我讲抗美援朝,我爸在朝鲜喝过老鼠尿,我想他也一定吃过老鼠肉。
毛之周:老鼠肉不难吃,味道比猪肉鲜美,我有一次跟干休所的老同志以考察之名去广东旅游,大家吃过某肉之后都说好吃,后来导游告诉我们,那是老鼠肉,很多人趴在路边干呕,我只是把恶心往下压,所以,我很平静。
停顿。
——对于吃过老鼠肉的人,他们别想拿他们的那种理论来恶心我了。我也知道,干休所的那些老同志仅是为了表示自己恶心,才假装干呕。其实,他们喜欢老鼠肉。他们会使自己显得很无辜。他们吃着不该吃的却一再证明自己没吃,或者,伸着头假装不知是某肉贪婪地去吃。他们都是一些食谱上、道德上十分检点的人。吃,对中国来说,是一门大学问,有位美食家,就写出了人肉方面的专著。
邓江:……鲁迅先生算美食家吗?他是左派吗?他为什么躺在虹口区院子里的地面上“嗷嗷”怪叫?
停顿。
他怪叫什么?他有羊角疯吗?他为什么闹得兄弟不和?
毛之周:他把死亡像定时炸弹那样装在自己的腑脏上。英雄是被制造出来的,人天生都不是英雄,英雄是一种主义的外衣披在草民的身上。
邓江:英雄的屎不会拉得像你这么长。真受不了你这种节奏,你真会磨时间的。你每次拉屎都花这样长的时间吗?
毛之周:如果,拉屎用一首五言绝句来形容进度,我才拉出“床前明月光”,正在拉“疑是地上霜”的“霜”字,还有“举头望明月”和“低头思故乡”憋在肚子里呢!屎,是好东西的残余。
邓江:如果你这是拉稀,也没有“飞流直下三千尺,疑是银河落九天”那种气概了。
毛之周:我已经失去那种少年英气了。
邓江:那你慢慢拉吧,我可打算走了。
毛之周:你不能走。你一走,我这就白拉了。
邓江:你总不至于说拉屎也是为了我吧?
毛之周:那我能为谁拉屎?
邓江:检讨你个人的历史……你的历史在一种阴冥里。你再也不能正视你的历史了,因为你的历史里充满着荒诞与不实,你为他人编造了一种历史。你自己也活着那种谎言里。
毛之周:我要说,历史研究是一个让自己遭罪的事情。在历史研究室,每一个人的德性都受到了挑战。可以说,我是唯一奉献出一切的人。
邓江:你们的历史研究室豢养着一些小说家。
停顿。
你有“一切”吗?你的“一切”是些什么?
毛之周:我已经失去了“一切”,上面要给我“双规”。
邓江:“双规”就是你的一切,我不会要你的一切,你把“双规”牢牢的抓着,不要再失去“双规”。
毛之周:可是“双规”不是我想要的。
邓江:你想要什么?法外之法都给你了,上面还会给你什么呢?
毛之周:钢筋、水泥、铁丝网已经形成了一个局,可是,你知道我是无辜的。
邓江:世界是什么?或者问,什么是世界? 谁能说世界不是一个“局”,我们能飞越大气层吗?宇航员失去与亲人通话权,他们能飞离人间多久?关键要知道,自己为啥进局?
毛之周:我都做了什么?我为什么要进局?其实,你知道,我不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,根本没想进政治这出戏里,更没有想成为时代的主角进政治局。我他妈干嘛要进这局那局的?
停顿。
我仅想走在我属于人的道路上。
邓江:可是,在历史里你已经被夺去了人性。古代的将领们有一种战袍,这种战袍穿起来沉重,但能够抵挡住外来的刀枪。你披着这战袍呀!
毛之周:我不需要战袍,我穿着草民的便衣。“穿什么是什么”,我就是草民。
邓江:每一个战将在取得卓著的功勋之前,都是和你一样的人,他们混在民众里,有的可能一辈子都出不了头。但当历史性的机遇到来的时候,他们就褪去庶民的形貌,露出英雄的形貌来。
停顿。
你掩盖着你的英雄气。
毛之周:可是法律在“规则”面前会倒下去,像虞姬倒在霸王的怀里。
邓江:霸王怀里应该揣着把短短的匕首,可是霸王喜欢舞弄长剑。也许他觉得长剑才体现气概,可是,政治家的气概需要体现在匕首上。你有你的匕首吗?
毛之周:民主不是匕首,至多只是菜刀。关于菜刀的传说,我已经不想在说了。我可不想像贺元帅那样一菜刀切下两个兵士的头颅,我们不应该谈一切带铁腥味的政治。我只想谈温暖的眼前,这暖暖的灯光,这被褥,这明亮的玻璃、晃眼的房间……
停顿。
这男人和女人的世界。
邓江:(惊讶地)你说男人和女人?
停顿。
你为什么要凸显性别的差异呢?你说,在你我之间本质的差异是什么?
毛之周:我们 ——其实——并无本质差异。
邓江:本质差异是一定存在的。你要先找到我们各自的本质,然后在寻找差异。
毛之周:我们的本质?男人和女人的,算是本质吗?这种差异体现了什么?
邓江:我要你忽视性别。在性别之外寻找本质,寻找差异。
毛之周:然而,除了性别之外,究竟什么是本质?我们的身体被放弃了,我们所从事的学说和事业是不同的。——我们都算文人吗?我研究历史,你画你的油画,写你的诗,你从事艺术。你的故乡和我的故乡处在同一个国度里,处在同一种政权下。我们的政治观念是相同或相近的,我们呼唤一种更好的政权,我仅希望能把自己关于故乡的梦想落在故乡。我们的差异很多,然而,本质……差异,我却找不到。
邓江:隔着一层蒙着臭气的毛玻璃,我看不清你,你也看不清我。你自个儿在里面释放臭气和烟雾,可是我却留在这里,听你的老调重弹。你难道没有看到我的厌倦吗?
停顿。
当你还在沉醉的时候,我已经厌倦了。可是,是什么力量让我到这里来?
毛之周:你说的难道就是存在我们之间那种本质的差异?你寻找本质差异性,我也寻找本质差异性。于是,我们在同一个地方找同一个东西?
邓江:我想这是,也不是我们相聚的理由。
停顿。
我们相聚是因为我们的共同点,我们都是寂寞的人。我敢断定,我们不是为了寻找本质差异而相聚的。否则,你应该与你的政敌聚在一起。
毛之周:严格来说,我没有政敌,因为我对政治并没有固定的目标。我只想强调,历史是一门科学,我不想生活在谎言里。作为一个想在历史中寻找真理的人,其实,我也想说出某种真实的东西,但那并不代表我会为真实牺牲自己。
我沉浸在当下的旋律里。某种程度上,我弹奏着音乐,我沉醉在历史感的音乐里。你的差别在于想把一切视觉化,让感知的世界流诸笔端。可是,对我而言,笔就是一本带着铁腥味的匕首,我讨厌笔了。
停顿。
我在厕所中沉醉,沉醉在便秘或者拉稀的快感里,我喜欢那种熏鱼式的臭气,可能你喜欢吃鲜鱼片,但这又有区别吗?是的,我也喜欢躲在厕所里抽烟,弄得烟雾缭绕的,仿佛让自己处在一个硝烟弥漫的岁月……然而,这一切,都不是我要研究的,写成关于历史的小说,或者小说般的历史。我不想再从旧纸中寻找历史了,我只想写点关于当下的历史。
邓江:你是说写点男女间的情情爱爱吗?在我看来,历史并非一种全景式的记录。深入创作,也是必须的。也许经过创作的历史才更真实。而如今,历史研究方面的专家的创作不是为了求真,他们沦为为魔鬼服务的工具。
你所说的当下的历史,在电视中上演着。
(邓江走向摆放在房间正中的电视机,打开电视)
电视传来声音:今日,我渔监船巡视钓鱼岛海域……
毛之周:做一个爱国分子是安全的,但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才是我们的国。
我们在哪里,我们就在哪里。我们改变不了我们的处地。我也想着揣笔巨款溜到国外去呢!可是,我有巨款吗?
邓江:(关掉电视)这叽叽喳喳的人间 ,究竟是什么鸟国?我们都是一些肮脏的人!
卫生间的毛玻璃门打开,一个秃顶的男子走进来,毛之周始终没有正面露脸,背影走到邓江站立的窗前。
(邓江转过脸)我是否应该回去?
毛之周:……你老公一定出去鬼混了,没准在约某个女人……
停顿。
你回去干吗?
邓江走上前去,拢住毛之周的脖子,开始亲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