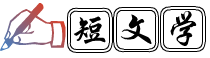窗外小水沟边竖立的木桩上,前两天系上了一条铁链,铁链的另一头系在一只半大的花狗脖子上,刚刚还在极其可恶的呜呜叫着。这只半大的花狗是父亲不知从哪里抓回来的流浪狗,虽是街头流浪者,并不算瘦弱,黑的狗脸,黑白相间的皮毛,卷曲着,有些脏乱。牵来时,一直曲着身子,夹着尾巴,一边呜咽着,全身发抖,时不时的冲着围观它的我们,吼叫几声。
我厌恶这条不速之狗,便跩着系它的绳,用力的拉扯,许是拽疼了,狗惊慌的嚎叫起来,不停地乱窜,想要挣脱。父亲叫骂起来,骂我黑心,我便放开绳子,自顾地走开了。我知道这狗的命运也不过是要成为一锅肉,被我们这些现在好心收养它的人分享,将它从街上的流浪者变作有窝睡觉,有稳定吃食的家养犬,待到用吃剩的米饭,骨头,汤汁养肥它,待到冬天,宰了它,剥掉皮,炖作一锅肉汤,啃完肉骨,喝上几碗肉汤,暖暖身子,算是对我们这些好心收养它的人的回报。我并不同情它未来注定的命运,反倒厌恶,因为它已经在我们面前摇尾乞怜了,大概是以为从今往后能过“好日子”。
毕竟是流浪者,做不来家养犬,了解什么时候该吠上几声,什么时候该安安静静地趴在地上的差事。待我困意浓了,熄灯睡下后,这遭瘟的东西,便开始不停歇地吠,扰了我的清梦。平日里若是别人扰我睡眠时,我心情是极差的,更况现在是这只我厌恶的狗,我便翻身下床,寻了一只长长的竹竿,誓要将它乱棍打死。
开了路灯,我立着棍子,叉腰站在它面前,这遭瘟的东西自是知道扰了我,蜷缩着躲到窝里去,呜呜地低吟着,狗眼躲闪着看着我,我怒目而视,瞪着它,欲举竿开打了,又怕是深夜,这狗东西痛叫起来扰了他人,心里便嘀咕起来:打死它么?吠的恼人,可恶之极。或是算了,原谅这畜生一次。站立一会后终是没有挥舞手中的长竹竿,将它乱棍打死。回屋继续睡下,清晨又被那不停地吠声惊醒,厌恶极了,后悔没将它乱棍处置。
恐怕是懂了我的杀心,这狗东西第二夜开始居然不再乱叫,若有过路的旁人,见过的不予理睬,生人吠上几声了事,白天毫不理会,不知情的人,许是不知还有这狗的存在的罢。既不惹我恼怒,我便不再起杀心了。年幼的侄女倒是十分喜欢,每日清晨开了门,必去呼唤,这花狗便从窝里窜出来,大力的摇着尾巴,上串下跳,一味的献媚讨好。我无事时站在它面前,也极力的来讨好我,我是不大理会的,且心里想着:无用的,我不打死你,你也活不长,到时候,只会落得更惨。
记得儿时,我也是爱狗的,养过一只,对我十分乖巧,外人却凶悍,浅灰色的毛,肥壮的很。后来却病死掉了,而后家里又养过,但却不那么招我喜爱。
我看过一部美国电影,主人公的弟弟在墙上贴上了小心恶犬的标语,却不是提醒别人,而是警惕自己,因那恶犬是在他的心里,恐会忽然地跳出来,做出疯狂的举动。我也有些相似,有时会忽然间的凶恶起来,对着别人叫骂,更甚者拳脚相向,仿佛心里也有只恶犬,会突然地跳出来,伤了人。我开始时常克制,严于律己,时日久了,这心中的恶犬也就变得温顺起来。年少的轻狂,便随时日渐渐远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