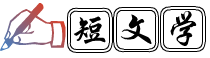1987年,交谊舞逐渐全面解禁,消失了十六年的交谊舞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。宜昌市开始流行交谊舞的时候,我们还在犹豫不决。这时候人们好像着了魔一样,厂工会各个车间的工会相继组织交谊舞学习班,厂工会每个星期五都要在幼儿园组织舞会,各个车间也抽时间组织自己的小型舞会。
厂工会邀请文工团的人帮助培训,各个车间则请已经在舞厅里淌过水的舞者来当老师。看着人们陆陆续续地跳进舞海,我们的心也动了,其实刚刚兴起跳舞风的时候我的脚就痒痒,内向的我不好意思。我悄无声息地在新华书店买了交谊舞的书,我们也悄悄地在家里学习交谊舞,老伴就是我在家练舞的模特,也是我在舞场上的舞伴。我不愿意求人,我是看着书,比葫芦画瓢,在家里学会了,我们才步入幼儿园的舞场。
她的悟性极好,一看就会,舞点踩的又好,跳得也很流畅。当然我们不是专业舞者,我们也不可能像全身心投入的舞者相提并论,那种标准的国际交谊舞,不是我们这样的人学的。我常常说,他们是正规军,我们是土八路游击队。他们是要的一种气场,要的一种被人羡慕的享受,我们是要的气氛,我们是锻炼身体来的。
舞场上成双成对,大部分不是夫妻,那时候出来跳舞的都是有一点爱好或是有头有脸的人,很多女性不好意思,所以舞场上的女性很少。那时候像我们一样,夫妻两个人在一起跳舞的人屈指可数,而且我们几乎就是跳全场。那时候她的体力充沛,舞兴十足,一晚上可以跳很多曲。
跳舞就显出她的人生另一面,她是愿意跳进社会的潮流中的,她想但是她不会自己来了的,叫她自己出来,打死也没有人相信,她是被我拉下水的。
开始的那几年,老伴就是我的舞伴,我基本上没有跟其他人跳过。九三年的一刀切,内退了,空闲的时间多了,白天该说的话都说了,晚上更加无聊,跳舞的人开始多了。一刀切的人当中,大部分都是女性,自然跳舞的也以大妈们为主,就是后来的广场大妈。
我们一层楼四家,三家都加入了交谊舞的行列,对门的一家也是两口子一起去,但是不是经常两口子一起跳。隔壁一家是我的同学,她是一个人喜欢上交谊舞,她又是她能够聊得起天的聊客。她家的那位是有点才,是没有去市里当公务员的那位,他不喜欢跳舞,他喜欢看别人下棋。
每天晚饭后一声吆喝,大家结伴而行。路上就有说不完的话,放下座垫继续聊天。我不会说也不知道说什么,就一个人默默地跟在后边。舞曲间歇她们坐在那里谈笑风生,我就像一个电线杆,戳在她的跟前。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,只要音乐声起,我就不由自主的动起来,很多人还没有听明白是什么曲子,我已经在舞场转了一圈了。
因此这也成了我的缺点成了她批评的理由。没有一个人会像我一样珍惜每一支音乐,曲曲不拉,很少有人和我一样,跳完整个晚上。
舞场是一个是非之地,是人们茶余饭后的佐料,就是风平浪静稍微不小心,也会掀起滔天大浪。
像很多人一样,这时候她也不能跳全场,跳上几曲就要休息一会。有她在我是不会去找其他人跳舞的,有她钦点的替补就是我们的邻居。也有三三两两的人凑过来和她打招呼,自然这些人就成了我下一曲的舞伴。
跳完一曲我继续立在她的面前,等着她开口说话,是跳还是让我和谁跳。
就像大多数夫妻跳舞一样,她会不断地指出我跳舞的不足。
“你跳快了。”
“你不要从别人中间插过去。”
“你跳舞,不要从旁边跳,要走中间。”
“你怎么这样跳呢?你看他们就不是这样跳。”
我的任务就是不住地点头说是。
转眼就是十几年,年龄不饶人,她都正式退休了。我们的邻居一家走了,他们回到自己的老家青岛,另外一家因为经常要去儿子那里也慢慢地不来了。
可能是见景生情缘故,没有了老邻居,没有谈天说地的朋友,没有了志同道合的舞场好友,老伴也慢慢地不愿意出来了。不过老伴还是隔三差五的过来看看,告诉我应该跟谁跳,不能跟谁跳,她又听到别人说了那些花边新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