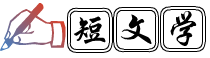2012年除夕
一个外表轩昂的二层小楼,矗立在一遍低矮的平房中。
雷政富,一个七十五岁的老人
雷霆,一个五十二岁的男子
雷震,一个四十八岁左右的男子
陶燕,一个四十岁的女人
正午,雷霆在一楼的大厅里看报,雷政富颤颤巍巍地在楼梯下的杂物堆中寻找什么东西。
雷政富:钳子在哪里?
停顿
我说钳子在哪里?
停顿
你听到没有,我在问你钳子在哪里?
雷霆:作为一名老党员,你要钳子做什么?
雷政富:我要拧紧那些该死的钢丝。你没看到我的洗脚桶已经快散架了吗?木板与木板已经不愿紧挨在一起了。可你只是在看那该死的报纸。
雷霆:爸爸,作为一名老党员,你怎么可以说《人民日报》是该死的报纸呢?
雷政富:你竟然也读《人民日报》了?
雷霆:我想从中看到人民有什么新的迹象。可你说它是该死的?
雷政富:我没有说报纸,人民并不生活在纸上。另外,你别老强调我的党员身份,好吗?我只想安静地生活在人民之中。
停顿
我说,你看到我们家那把钳子吗?
雷霆:爸爸,你原本挺自负的,一直像稻田里的一株稗草立在我们这些喜欢垂头丧气的小民中间。
雷政富:(狠狠地瞪了雷霆一眼)你竟然把我比喻为稗草?你以为自己才是稻谷?而我仅仅需要一把钳子!
停顿
说真的,我真地希望你们都能离开这个家。我可不希望生活在你们这些稻谷中间。
雷霆:爸爸,你虽然是一株稗草,但是,我们没有人否认是你为我们带来了粮食。没有你,我们只能生活在野外,忍受风吹雨打。我们已经习惯在你面前低头了,谁叫我们将成果放在自己的脑袋里?可是,爸爸,我不当钳工已经很多年了。我发誓我已经有两年没看见过那把钳子了。
雷政富:你说那把钳子,你一定还记得那把钳子吧!
雷霆:我当然记得那把钳子,它从不生锈,你说过它是用精钢做成的。那是你从日本带回来的。你也说过,中国是做不出那么好的钳子。
雷政富:呸!我竟然污蔑我从日本带回一把钳子?
停顿
我说过“中国做不出一把好钳子”这样的话吗?
雷霆:你说过。
雷政富:就算我说过吧。那可不是一把日本钳,你没有见过上面的德文字吗?那是一把德国钳。但是,你还记得那把钳子的来历吗?
雷霆:我当然知道,爸爸,那把钳子跟你的党费有关。
雷政富:跟党费有关?你怎么扯党费了。
雷霆:我是说那是上面奖赏你的。
雷政富:幸亏你没有说,那是希特勒赠送我的钳子。
停顿
但那确实是我们家收到得第一件来自国外的物品。那真是一把好钳子。
雷霆:我记得,在我们家那只锈迹斑斑的工具箱里,每件工具也都锈迹斑斑,只有那把来自德国的钳子是白净的,时刻闪动着金属的光泽。它知道什么是它的本分,使命在哪里?它完全不同于我们的工具。
雷政富:孩子,你不要再说下去了。我知道你的言外之意了。你总是对老爸不满,但你也要知道,爸爸作为一名党员,可也是从来不不生锈的。
雷霆:爸爸,我没有说你是工具。如果你是一件工具,放在一个满是锈迹的工具箱里,你不生锈是难以想象的。
雷政富:我什么时候生过锈?
停顿
难道你想说,那把钳子是不存在的吗?
雷霆:不,它一定存在过。它从净火中走来,来到我们家,在我们家生活了一段时间,我们曾经用它干过些什么?剪断公家的一段电线,连接起自家的风扇?用它剪断钢丝床边缘的毛刺?拧紧马桶圈箍,还有你该死的洗脚桶?
雷政富:你不能说我的洗脚桶是该死的,它是为我的脚而存在的。你骂我的洗脚桶就是指桑骂槐地骂我的脚,我的脚可是为这个家立下过汗马功劳。
雷霆:爸爸,我没有骂你的脚,你的脚虽然天生畸形,也从来没为我们家立过什么功劳,但是我从来没有歧视过它。它毕竟只是你的脚,不是我的脚。如果是我的脚,我宁愿不要脚了。
雷政富:我的脚怎么没为这个家庭立过功劳啦?大串联时期,我们没有马可骑,也没车可乘,我只有靠我的双脚。——我到底还有没有让你欣赏的地方?
雷霆:爸爸,你有,至少你的脑门是闪亮的。
雷政富:你一直羡慕我的谢顶吗?
停顿
至少,我有一件你没有的东西。
雷霆:爸爸,你是说你的年纪吗?你要相信,我会活到你这样的岁数的。你已经到了生锈的年纪了。时间会吞噬你的。
雷政富:你怎么能跟一个老人扯他的年纪?我说的是,你没有党证!
雷霆:那个红色小本本?这个我确实没有,但是我有计划生育证啊,外形跟那个差不多。
雷政富:外形?你这个浅薄的人!国徽怎么能与党徽相比?况且,怎么能只看到外形?你没有看到他们有不同的内涵吗?
(雷政富气呼呼地走到雷霆面前,一手扯过他手中的报纸)
雷霆:内涵?我看到了呀!它们里面都有猩红的印签。其中的一个印签盖在了屁眼上,党准许我放屁了。
雷政富:(雷正政富抖动着那张《人民日报》)《要创造机会让人民批评政府》。我们的党什么时候不准许你放屁了?你一直没有停止过放屁。你还记得你同学给你起的诨名吗?
雷霆:爸爸。你是想说“放屁大王”吗?如今,某个报纸早已掠夺了那个雅号了。我再也不放屁了,我仅说些人话。
停顿
爸爸,你是说你要修你的洗脚桶。你的洗脚桶有什么信仰吗?它信仰温水,还是你的脚?木板与木板都是它的成员,可木板与木板根本没有信仰可言,它们走到一起并不是为了容纳温水,也不是为了你的脚,是钢丝所形成的强大的纪律,才是它们不得不待在一起。它们没有散掉,也仅仅是因为害怕被当成柴火烧掉。
雷政富:木板的最终命运都差不多。它们不可能万寿无疆。
停顿
可爸爸是个有信仰的人。
雷霆:我知道,党派和宗教派别一样,都是有自己信仰的,他们怎么好意思承认自己工具化的人生。爸爸,作为一名党员,你信仰什么?
雷政富:我曾经信仰某种主义,后来,我一直信仰“上帝不是万能的,但没有金钱万万不能”。
雷霆:爸爸,你扯金钱干什么?我知道你并非完全信仰金钱?
停顿
在那个艰难的时代,你无耻地出卖了妈妈。
雷政富:我没有出卖你的妈妈,我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出卖你的妈妈?你的妈妈仅仅是被他们揪出来的?
雷霆:他们为什么要揪出妈妈?他们难道不是和你一样的人吗?我知道,他们中很多人也持有党证。
雷政富:你的妈妈不应该说“毛主席也不能万寿无疆”这样的话。
雷霆:可那是每个正常的人都应该有的认识啊。亏你还说自己是个有信仰的人,你们信仰什么呢?
雷政富:你的妈妈可不是死在“被揪”这件事上。
雷霆:北京每次开会都会一个精神,那些“精神”让我妈妈得了精神病。是不是说北京也得了精神病?你对妈妈都做了什么?
雷政富:你妈妈得了病后,我可是对她照顾有加,那时候,你兄弟俩还小……
雷霆:我就记得你曾经“照顾”她的情境,你把她“照顾”得口鼻出血了。
雷政富:她得了精神病后更加反动了……我不照顾她,就会有别人来照顾我……我们都是被逼的。
雷霆:谁逼你们了,爸爸?你是洗脚桶上的木板吗?有人会用钢丝箍制你?
雷政富:孩子,你不能理解那个时代。这怨不得你。
雷霆:这个时代就不是那个时代吗?我怎么觉得至今还活在那个时代啊!
雷政富:孩子,你看看报纸都怎么说了“应该允许人民批评政府”,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。
雷霆:但我觉得那个时代还会回来。或者说,那个时代还没有过去,没有人深刻地检讨现在和过去,那个时代就是这个时代。
雷政富:报纸已经说了,我们的制度存在问题。
雷霆:可是,它既要人民直言,又要人民维护某个制度。这是什么时代?还是那个“毛主席万寿无疆”的时代吗?
停顿
爸爸,今天是除夕了,你知道除夕是个什么节日吗?
雷政富:除夕,就是除去了往昔,跟过去说拜拜了,让过去滚他妈蛋了,让新的时代开始了。
雷霆:那么,容许老百姓放鞭炮吗?
雷政富:老百姓当然可以在烟花爆竹里解放了自己。
雷霆:烟花爆竹能让他们获得解放吗?
雷政富:其实,老百姓不管自己自由不自由,他们只要快乐不快乐。
雷霆:他们快乐吗?
雷政富:他们当然快乐。听,烟花绽放了,爆竹响起来了。老百姓很快乐。
雷霆:可是,除夕,应该给妈妈上点香吗?
雷政富:已经上了,你没有看到你妈妈正在享受香火吗?
雷霆:香火围绕的脸庞依然是严峻的,但是,你为什么说她在享受香火呢?
静场
到底是谁在享受香火?
雷政富:你为什么要说你妈妈得脸庞是严峻的?你没有看出她的慈爱吗?
雷霆:爸爸,你难道忘记了妈妈死的时候,她双目圆睁,不肯闭眼吗?她只有在精神病发作的时候,才放声大笑。可是你害怕她的笑声。所以,她总是很严峻。
雷政富:她死后是慈祥的。
雷霆:你伪造了她的遗容,你想给我们制造一个慈母的形象,可是,我们知道她死得很凄厉。
雷政富:她留下你们哥俩,她是幸福的。
雷霆:人民总是幸福的。他们没有理由不幸福,是吗?
雷政富:是的,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幸福的。
雷霆:可是,爸爸,我们不幸福。
雷政富:你们为什么不幸福呢?你弟弟曾经对我说过,他是幸福的。
(门突然打开了,雷震携着陶燕站立在门口,朝里面张望了下,然后走了进来)
雷霆:(转向雷震)你幸福吗?爸爸说你是幸福的。
雷震:我幸福呀!我当然幸福。
雷霆:你幸福什么呢?
雷震:我幸福是因为我活着,能够听到遍地燃放爆竹的声音。
雷霆:爸爸,雷震是幸福的。你赢了。
雷政富:该死!我赢了什么?你们幸福不幸福关我屁事?
停顿
陶燕:(妩媚地笑着):爸爸操心劳力都是为了我们幸福。我们当然很幸福呀。
雷政富:我在音乐学院当院长的时候,我总是跟教师和学生们讲,人就像诞生在琴弦上的音符,飘荡着,在自己还能够被别人听到的时候,要让音色纯正。因为,在任何一首乐曲中,都不能仅有你一个音符,属于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,你飘着飘着就会远去,消失在空气之中。可是,你如果想成为主旋律的一部分,你必须符合作曲家的意念。
停顿
是作曲家让你们诞生的,你不能单独在历史的琴弦上跳动。可是,你们仅给我的晚年生活带来噪音。你们能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吗?
雷震:爸爸,我们不是音符,我们是乐手。我们要演奏自己的旋律,时代没有赐予我们好的作曲家。你们的音乐学院,有作曲系吗?我怎么只记得你们学校走出来的都仅是些乐手?
雷霆:爸爸,你懂音乐吗?你被上面派到音乐学院当院长。学院的教授们是否在音乐上崇拜你?他们把你视为音乐大师了吗?
雷政富:你们知道,爸爸年轻时仅喜欢吹吹口哨。可是,学校里没有口哨专业,我泯灭了自己的专业。作为院长,我不参与学校内的汇报表演,我时常作为嘉宾观众。
停顿
社会上,人们有着把吹口哨当成流氓行为的偏见,我仅能在深夜里吹吹。在你们小时候,喜欢听我的口哨声,你们是怎么获得音乐素养的?你们兄弟俩都喜欢听《朋友们,再见!》,要不,现在我给你们吹一段?
(雷政富抿起干瘪的嘴巴,口哨声响起)
雷霆与雷震(跟随口哨一起,唱到):朋友,再见吧,再见吧,再见!……如果有一天,我们在战场上相遇……
(陶燕在一旁跟随曲调按节奏击掌,模样为歌声和口哨声陶醉。全场人员都手舞足蹈起来,场面陷入兴奋)
曲终
雷政富:(微喘着)看你们多么喜欢我的口哨。我们大家都是幸福的。
陶燕:爸爸,我们本来就是幸福的。
雷霆:只有艺术能拯救我们。我只有在艺术中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
雷震:你们干嘛要讨论幸福与不幸福的话题?幸福,或者不幸福,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意义?你们一定要给生活贴上这种标签吗?是否,你们也要给空气贴上“清洁”或者“不清洁”的标签。
陶燕:是啊,一切都需要被指称清晰。每个城市不是在做PM2.5检测吗?我们需要告诉民众这里有什么情况,空气有多么的净洁,人们是否幸福?
雷霆:可是,没有人检测地下水源,没有人检测各种混入食物中的化学药剂,没有人检测人们的意识……
雷政富:好了,不要褒贬社会,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,首先要做好自己。一个做不好自己的人,是没有权利指责社会的。大家都不要忘记,这是一个全家聚会的节日,不再允许让社会问题渗入家庭中。
雷震:我们要将问题关在门外。我响应爸爸的号召,下面是畅享美味的时间,是品味爸爸厨艺的时刻!
陶燕:是否应该放一挂爆竹庆贺一下?
雷政富:爆竹就不要放了,你们都没有为我带来孙子。
陶燕:爸爸,孩子死活希望去外婆家,不喜欢到这里来。
停顿
雷政富:我不想让龙年的问题拖延到蛇年。……我还没有找到我的钳子。
雷震:爸爸,我给你买了只带电动按摩的洗脚桶,你再也不需要那只破木桶了。它就放在外面的车的后备箱里。
(转脸对陶燕):你去把洗脚桶拿来!
(陶燕应声走了出去)
雷政富:是塑料那种吗?我讨厌塑料,我喜欢木头。
停顿
况且,这洗脚桶会让我回忆起你们的妈妈。
雷震:妈妈跟洗脚桶有什么关系?
雷政富:这是她所剩下的唯一的嫁妆……
雷霆:爸爸,你为了忘记妈妈你将她生前的那只红漆木箱都扔了,可是你却保留着洗脚桶。是不是因为洗脚桶能够给你带来较为实在的幸福?
雷政富:我不能完全地生活你妈妈的时代,我必须走出你妈妈的生活。
停顿
但是,我并没有完全忘记你妈妈。
雷霆:在家庭聚会的时刻,我们应该给妈妈留下位置。
雷震:按摩洗脚桶的到来,并不是要你把木桶扔了。
停顿
爸爸,你是一位善于制作咸鱼、灌制腊肠的优秀党员,你做菜的手艺不错,注重生活,是人民居家过日子的好榜样。最令我回味的是你制作的酱。
爸爸,你的酱是怎么做成的?
雷政富:你妈妈教会我怎么做酱,那是你妈妈在文革前留下的手艺。香气浓郁的酱,总是能够唤起你们对旧日的回忆,觉得一切还处在以前,你妈妈还活着的时候。
停顿
那是清贫而温馨的日子。
雷震:(面对着雷政富所在的方向,弯腰系着松散开来的鞋带)爸爸,我以系鞋带之名给你鞠躬了。
雷政富:谁要你鞠躬了?你们都把腰给我挺直了,在家里也不例外。你知道人的高贵气质从什么地方来?
静场
雷震:在这个除夕,我们还有那酱可吃吗?爸爸。
雷政富:酱是我们家必需的调味剂,比任何酱都要好吃,对我们也意义重大。
雷霆:可是,爸爸你从来没有说过那是妈妈传下的手艺。
雷政富:我并非要做每件事都给你们讲清来龙去脉。
雷霆:可是,妈妈一定不会将酱放在鸡舍上晾晒。
雷政富:晾晒是制作这种酱最为重要的的工艺之一。
雷霆:我没有说不要晾晒,我只是说不要放在鸡舍上晾晒。
雷政富:那我们家还有什么更好的地方晾酱吗?
雷霆:你为什么又要养那几只鸡呢?似乎你对有翅膀的动物情有独钟。
雷政富:我仅是想找回一定田园的乐趣,难道不可以吗?
(陶燕提着一只色彩鲜艳的塑料洗脚桶走进屋来)
陶燕:(将塑料洗脚桶放在角落里)你们怎么又谈论起鸡来?难道你们不怕禽流感吗?
雷震:他们其实在说酱。
陶燕:酱怎么啦?
雷霆:酱里落进了鸡屎。
雷政富:那鸡屎已被我舀了出去,那依然是好酱。
雷霆:可是,爸爸,我说的仅是我看到的那抛鸡屎。你怎么让我们相信,酱里没落进更多的鸡屎?
雷政富:我以党员的人格保证,那是好酱。
雷震:爸爸,党格无法保证鸡不会去跳进酱缸里去刨酱。这个酱——我们不能吃。
雷政富:你们都不再爱你们的妈妈了。
陶燕:爸爸,每个人都爱自己的妈妈。
静场
雷政富(极为生气在楼梯口的工具箱寻找):我一定要找到那把钳子。钳子没有翅膀。
雷震:爸爸,你是在找那把精钢钳吗?
(雷政富转过脸,怔怔地望着雷震)
停顿
我早在一年以前……
(语音转入低戚,无人听到那把钳子的下落)
剧终